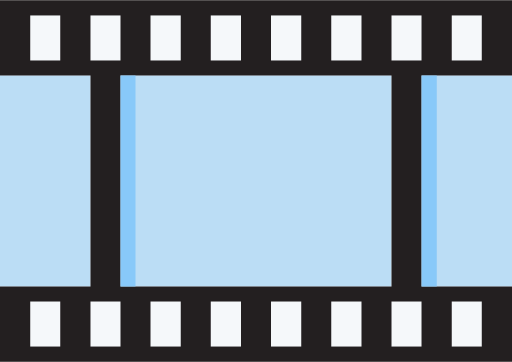劉沛弦 | 學習經驗分享-態度與思考上的衝擊
Story|劉沛弦
態度與思考上的衝擊
工院19級,2019年6月21日至 2019年9月5日期間至美國華盛頓大學作為一名交換生。
學校介紹
華盛頓大學是西雅圖公立大學,座落在 lake union 之北。而我們所去的生物物理部門 (PBio) 則位在醫院內,但研究方向是基礎科學而不是醫學應用。Dr. Rieke 的實驗室屬於生物物理部門,顧名思義即是用物理的思維以及現有物理領域的工具來研究生物現象。他們研究的生物領域是視網膜的運算方法,也就是想問以下類型的問題:
視網膜是如何有效率的壓縮光學訊號以傳遞至大腦?已知視網膜的光受器細胞(photoreceptors, 即接收光訊號的細胞)數量遠大於視神經細胞(retina ganglion cells, 輸出電訊號的細胞)的數量,因此在視網膜內部必然有某些訊號處理,才能有效的壓縮資訊量。什麼訊號處理方式會是最有效率的?視網膜的處理方式是否是最佳解?現下已經知道某些視網膜神經網路的功能(例如有些細胞只對某種方向的刺激有反應、有些只對由遠而近的刺激有反應等等),而這些功能是如何產生的?這些功能是來自單一上游神經細胞還是來自整體網路?
Rieke lab 中研究以上問題的方法是電生理,可由cell attached recording、whole cell voltage clamp、whole cell current clamp等方法紀錄從光受器細胞一路到最下游的視神經細胞的反應。這些即是我們此行學習的目標技術。
心得報告
實驗方面
我在清大的實驗室是以理論及模擬為主的實驗室,因此到Rieke lab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學習實驗技術,而無論之後是否會做實驗,了解實驗的限制以及取得方式有何優缺都是非常有用的經驗。
電生理實驗有四個主要步驟:實驗前的準備、解剖、紀錄以及收尾 (preparation, dissection, recordings and clean up)。其中解剖與紀錄是技術的核心,而Dr. Rieke也以跳脫順序的方式由紀錄的部分開始教我們,再來才是收尾及準備(沒有教解剖是因為解剖在其他電生理實驗室也能學習,而紀錄則是少數擁有patch clamp技術的實驗室才能做的)。到了暑假中時我學會了cell-attached recordings,而維屏更是學會了whole cell recordings。對我來說最令我佩服的是Rieke lab在實驗器材上的用心。舉例來說,在紀錄時視網膜是被黑色屏幕遮住的。這是因為被分離出來後的視網膜接受到可見光照射後會快速死去。因此無論是換針或調整載台等等都必須要把手伸入屏幕中,摸黑調整。而實驗中最害怕發生的事情之一就是溶液溢出,流到顯微鏡上。如果發生了這種事,則顯微鏡需要直接送修,會一兩個禮拜無法做實驗。然而因為顯微鏡連同視網膜都被屏幕遮住了,因此沒有辦法看到溶液是否有溢出的現象。於是Rieke lab做了三層的防護:在主容易輸出管旁邊再安裝第二個輸出管,而如果主幫浦故障第二個幫浦就會自動開啟。若兩個幫浦都故障了,則載台外頭還刻了一層溝槽,因此溢出的水就會從溝槽流出。除了設備上的層層防護外,做實驗時Dr. Rieke也時常叮囑我們要注意廢液槽的水管是否持續有水注入,如果沒有則可能是溶液即將用盡或者幫浦失效。雖然我沒有做過實驗,但還是能夠欣賞這裡的設備的齊全及人性化的設計。Dr. Rieke 十分在乎實驗的控制變因必須要盡量在實驗者的掌控之中(例如溫度、盡量少讓視網膜接觸多餘光線等等),而我認為這反應出的是實驗學家的專業,因為唯有這樣才能確保實驗數據的可信度。
另一個講求專業的例子是好的實驗學家能夠看著示波器來斷定實驗是否出錯或即將出錯,而依此判斷臨場應變。例如若電位圖顯示產生動作電位後過極化太多,則代表電極很有可能快刺穿細胞膜了。這時就必須要適當的給予電極正氣壓,讓它與細胞膜有適當距離。又例如若溶液用盡而忘記換新的話細胞就會開始缺氧,而這會反應在細胞的活性降低上。這些都是很小的細節,卻可以區分出實驗學家的專業程度。
|
|
|
|
圖一。左圖是用電極接觸細胞 (cell-attached recordings) 在confocal底下的畫面。右圖是視網膜在顯微鏡底下的畫面。 |
|
以理論及模擬訓練的人來看,最重要的啟示應該就是面對實驗數據要小心檢驗,不可輕易相信。對於跑模擬的人而言,測試理論是否正確的受體是電腦,而電腦出錯的機率小之又小,因此對於數據缺乏實驗學家所具備的疑心。例如在暑假前幾週,我們正嘗試著要找出數據太過不穩定的原因,而任何Rieke lab與陳老師或焦老師實驗設備上的不同都是需要納入考慮的。其中一個不同之處是刺激的光強度,而後來發現如果對於在台設備的光強預估值正確的話,那這個光強很有可能讓細胞的反應變得不穩定。另一個可能因素是適應性 (adaptation),在台灣的實驗室通常沒有等待細胞適應平均光強 (mean light intensity) 的動作,但Rieke lab會等約1-2分鐘讓細胞適應。稍微測試後發現讓細胞適應才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沒有適應會導致不同時間點上細胞對相同刺激的反應不同,有違實驗所追求的可重複性。如果對於中間的這些小細節不清楚,則理論學家很有可能就把不好的實驗數據也照單全收,而建立在此之上的理論則也可能受影響。除此之外,了解實驗上受到的限制可以促進有效溝通,理論學家也會較不「天真」一些,做出的理論模型與實際生物體可能較有接軌。並且了解限制後,理論學家更能與實驗學家討論,以適法設計出實驗讓自己的理論被應證。
總結來說,與實驗的接觸讓我對實驗有了新的認識與興趣。對我來說實驗與理論各有魅力所在:實驗能讓操作者親眼證實甚至發現某個現象 — 也就是說,如果你對於某個現象有興趣,但現有的資料不多,你可以親手開闢關這個領域,帶領大家發現新的資料。如果有一個現行的理論,你可以親手驗證或否證它。這對我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為做理論對我來說最麻煩的地方是往往會問自己「這些東西真實存在於生物系統中嗎?」或「我這樣簡化可以嗎?」等等問題,而實驗正是可以彌補理論上的這些不足。
|
|
|
|
圖二。由左而右是我和維屏,分別與我們最常用的那台儀器 (confocal) 合影。 |
|
理論方面
除了學習實驗技術外,理論部分也持續進行。我建了一個十分簡化但卻也能夠預測訊號的模型,目前看來也能定性描述實驗結果。我雖然主要是自己做,但也有需多人給了我很有用的建議,如Dr. Rieke, Dr. Eric Shea-Brown, Dr. Stephanie Palmer, Matthew, Gabrielle, Adree 和 Timothy等。Dr. Shea-Brown 和他的學生 Stefano 及 Matthew 其實正在做一個與我們的非常類似的題目:神經網路是如何擷取潛在變數 (latent variables) 的?差別是他們著重的是要知道神經網路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性才能夠計算出潛在變數,而我所建立的簡單模型正好符合他們所認為需要擁有的特性。這就回到了剛剛所說的理論的魅力了。理論可以讓你跳脫現實的框架與束縛,變數由你自由操控,機制任你自由想像。研究生物一個最大的障礙之一就是複雜性,因為有太多生物機制同時運作,我們往往很難找到某個現象真正發生的源頭。當然,或許有許多現象正是需要這種複雜性才能運作,但從現行文獻看來也有許多現象雖然看似複雜,但其實將機制簡化後仍然可以運作。簡化的優勢又是什麼呢?對於一個現象,我們當然可以很冗長的敘述它,例如:A啟動B,所以B和C結合……,或者我們可以用一個抽象但簡潔的方式描述它。後者往往具備概論性 (generality),以單隔室神經細胞模型 (single compartmental model) 為例,若先單純考慮動作電位的產生而不考慮穩定性等等,我們其實不必特別在意到底是哪些離子通道造成動作電位的,也不用擔心某顆細胞多了某個離子通道就必須要重新去審視這個現象等問題。目前所知的動作電位都是透過某種分岔 (bifurcation) 造成的,而只要知道是哪種分岔,我們就可以描述出該動作電位會長什麼樣子。
某位神經科學家曾說過,「神經科學的原理」這本書每年增厚,原因是我們雖然總是再發現新現象,卻往往無法理解它,因此所謂的「原理」只能不斷往上加。但當我們真正了解現象時,其實就可以把它歸納為少數幾條原理,如電磁學之於馬克士威方程式一般。這是在神經科學界中,實驗與理論脫軌的問題嚴重所造成的。這也是之後如果我打算繼續研究理論的話,會想要正視的問題。
|
|
|
|
圖三。左圖為我和Dr. Rieke討論東西時拍下的部分白板 (樓下的理論中心連玻璃都無法幸免於難,都被當作了白板使用)。右圖為實驗數據分析。 |
|
實驗室環境方面
我認為Rieke lab最棒的地方不是他們一流的設備,而是一流的人才。Rieke lab的學生不一定絕頂聰明,但和他們談論科學時他們總是會不自覺留露出對科學的熱忱。例如Julian的其中一個休閒嗜好是幫吸血鬼建立吸血模型,還打算發表在關於科幻的小期刊上。Chris是人體維基百科,對於不只是視網膜和物理,問起其他科學領域甚至於人文社會他都能說得頭頭是道。Gabrielle和Adree邀請我參加了他們的讀書會 (mini journal club),我們會每週定期討論我們有興趣的論文,而從中可以聽出他們對很多現象是打從心底非常好奇的。這些人的工作時數都不長,甚至我和維屏往往是實驗室中留到最晚的人。但短的工作時數卻完全沒有反應在他們的學術成就上。這裡每個人的進度報告都令我驚豔,不僅是進展快而已,完整性、對問題談討的深入程度幾乎都到了苛求的境界。而從許多人看待問題的方法上其實都能夠看到Dr. Rieke的影子。Dr. Rieke自己當然是一個很棒的老師,他總是能一針見血看見問題的核心,也總是能看見一個現象背後的物理意義。他教學時則是非常有耐心,在實驗室會議報告自己的研究時會非常鉅細靡遺的解釋所有細節,也會在確認所有人都跟得上後才會繼續。我覺得實驗技術與對理論的建議都非常珍貴,但此行最重要的還是與這些人相處的過程。只有在好的環境下人們才會成長,而好的研究態度和思考模式對科學家而言更是十分重要。用言語著實難以形容Rieke lab對我在態度與思考上的衝擊,但我只能說這是我此行學到最重要的一課。
|
|
|
|
圖四。左圖由左而右是我、Dr. Rieke和維屏。右圖由左而右是Todd, 維屏, Adree, Gabrielle, Julian, Chris 和我。 |
|
其他
食衣住行
美國的食衣住行我只有一個字形容:貴。 也因次非常感謝工學院學士班的支持。
西雅圖是一個對華人非常友善的地方,有華人市場、台式中式日式韓式料理應有盡有。這裡的華人圈也不小 — 我們實驗室有兩間辦公室,我們這間在我和維平加入後華人人數就過半了。因此在這邊不太需要擔心文化衝擊。對我而言最大的文化差異可能是交友圈,因為在台灣最親近的朋友往往就是同學、同事,但在西雅圖他們將工作與私生活分得很開,因此大家都有自己本來的朋友,外人要加入稍嫌不易。甚至是我和維平加入之後實驗室才比較常一起活動,包括一起聚餐、露營等等。
工作時數
我覺得西雅圖很值得學習的點是責任制。我們實驗室中甚至有人以「因為禮拜五來工作會想回家,所以乾脆就待在家工作」為由,禮拜五從不出現。但如上所述,他的實驗進度非常的完整且深入。在台灣,雖然學術圈不是強迫性的打卡制,但會有這樣的潛在壓力。台灣人似乎有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努力就會有成果」等等想法,雖然不一定不好,但卻嚴重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品質。美國人覺得生活也是很重要的一環,不能因為工作就完全拋棄,因此他們的生活品質遠遠高於台灣。在台灣,大家總是9-5的工作,卻沒有時間停下來好好休息。但休息卻往往是創意的來源 (至少對我來說),雖然馬不停蹄的工作似乎能夠做完很多事,但除了可能沒效率外,更有可能沒品質。這點不僅僅是個人在工作習慣上值得省思,更是台灣整體教育值得省思的。